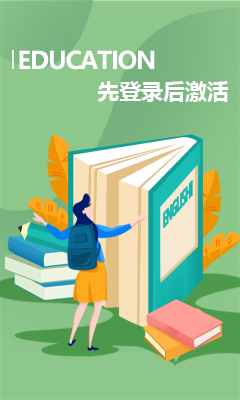國際教育“吸走”生源?王殿軍:公校教育急需反思
記者 | 江敏
盡管分屬不同體系,但國際教育的迅猛發(fā)展也讓公校教育者們開始反思,該如何提高吸引力以留住生源。
從今年三月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數(shù)據(jù)來看,2018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(shù)為66.21萬人,較上一年度增加5.37萬人,增幅8.83%。
不止是留學生,國際學校數(shù)量增加也側(cè)面反映國內(nèi)家庭對國際教育需求的上升。據(jù)K12國際教育的資源聚合平臺頂思發(fā)布的《2019年全國國際學校圖譜與行業(yè)發(fā)展報告》顯示,截至2019年9月30日,全國(不含港澳臺)新增60所國際學校,總數(shù)達到1168所。
“在公立教育尚未變得更好的時候,有些家庭選擇離開這樣一個體系,作為公校校長,我感到非常痛心。希望我們能夠快點改變,讓本國教育接近世界水平,能夠讓孩子待在自己國家和父母身邊接受最優(yōu)質(zhì)的教育。”清華附中校長王殿軍近日在頂思RAISE大會上表示。
從2007年開始,王殿軍擔任清華附中校長,并在校內(nèi)推進一些列教育改革,比如將大學先修課程引入高中階段,用“綜合素質(zhì)發(fā)展積分系統(tǒng)”評估學生,以及采取集團化辦學將教育資源輻射到薄弱學校等。盡管這些措施在本校獲得反響,但這并不能代表公立教育整體變化。
在很多維度上,中國公立教育發(fā)展的確能被稱之為“奇跡”。我國從1986年頒布《義務教育法》確立普及義務教育制度后,到2000年正式完成目標共花費15年時間。“以最短時間實現(xiàn)義務教育普及,高中教育基本普及,大學教育也實現(xiàn)了大眾化,這些成就對一個人口眾多、經(jīng)濟起點低的國家而言,實屬難得。”但王殿軍認為,從成果來看,我國教育水平還未趕上發(fā)達國家。“從我國諾貝爾獎獲得者與整體人口數(shù)量之比就能看出來。”
王殿軍認為,公校在許多方面急需變革。在因材施教、能力培養(yǎng),以及跨學科等方面,國際教育可以為公校變革提供思路。
公校往往從統(tǒng)一教學大綱和標準出發(fā)來設計課程,使得“因材施教”難以實現(xiàn)。相比之下,國際級學校盡管不允許使用境外教材,但在課程設置更為靈活。因采用小班制教學,國際學校師生比多在1:15左右,甚至更高,這使得因材施教的可實現(xiàn)性更強。
另外,公校往往因教學任務以知識點掌握為主,忽略對學生能力的培養(yǎng)。王殿軍坦言:“‘以能力為中心’,通常只落實在口頭上,或是校長匯報材料、局長們的講話里,而沒有融入教學評價體系中。”再加上公校評價學生的方式更依賴考試分數(shù),學生很容易成為知識裝載容器。“怎樣用更豐富的維度來評價學生,引導健康教育,也是中國教育急需改變的地方。”王殿軍說。
但公立教育想要完成變革仍需時間。我國各地區(qū)教育實踐不一致,發(fā)展水平難以達到均衡,這些現(xiàn)實狀況已經(jīng)給頂層設計制造難度,落地實踐則難上加難。
國家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,對招生考試制度全面改革。2014年9月,國務院正式頒布《關(guān)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》,這一綱領(lǐng)性的文件標志著改革實踐的啟動。
“但改革只邁出了非常小的一步,到現(xiàn)在,全國不到超過一半的省進行了高考改革,改革力度也很小。想讓所有省都邁上一大步,還需要假以時日。”王殿軍評價道。
當然,盡管理念可鑒,但國際學校作為舶來品在中國發(fā)展僅有十多年,其運營經(jīng)驗和教學實踐還遠談不上成熟。“有一些早期的國際學校完全忽略了自己是在中國,中文學習與其它第二外語之間并無區(qū)別。”在王殿軍看來,國內(nèi)的國際教育雖然從西方引進,但如何做好本土化是一個難題。
政策因素也給國際教育的發(fā)展帶來不確定,公立學校國際部的存在就遭到質(zhì)疑。質(zhì)疑聲認為,雖然學校有辦學自主權(quán),但國際部也會擠占公有資源。“教育界對此看法也不一致,有些地方已要求公立學校剝離國際部。”王殿軍評價道。
對國際學校而言,經(jīng)營層面的辦學紅線,以及招生和教材使用的政策為其發(fā)展限定范圍。這也使得無論其規(guī)模發(fā)展多迅猛,依舊無法“獨自美麗”。而從國際學校生存的大背景來看,王殿軍認為,如果無法推動本國教育向前,國際學校發(fā)展再快也不能稱完成了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