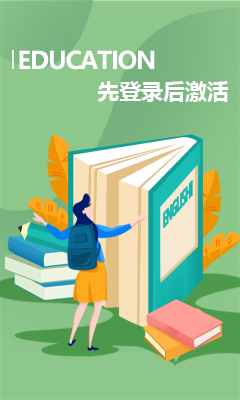基礎(chǔ)教育“減負(fù)”,有人想過(guò)高等教育的危機(jī)嗎?
近日浙江、南京出臺(tái)的減負(fù)新方案,讓中小學(xué)生“減負(fù)”再次成為輿論關(guān)注的話題。其實(shí)早在20世紀(jì)90年代中期,教育主管部門就開始呼吁“減負(fù)”。然而,“減負(fù)”折騰了近20年,不但沒有顯著收效,反而陷入了極為尷尬的境地:不“減負(fù)”吧,有一部分學(xué)生整天抱怨學(xué)習(xí)太累;一旦真的“減負(fù)”,許多家長(zhǎng)就開始恐慌了,生怕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。客觀事實(shí)早已證明:“減負(fù)”并不能夠解決我國(guó)教育領(lǐng)域存在的根本性矛盾。“減負(fù)”—>無(wú)效—>再“減負(fù)”的循環(huán),如同行為藝術(shù)。
為什么我國(guó)基礎(chǔ)教育階段,中小學(xué)生的學(xué)業(yè)負(fù)擔(dān)會(huì)顯得很重?因?yàn)槲覈?guó)高等教育機(jī)構(gòu)以高考作為主要選拔機(jī)制,現(xiàn)實(shí)中基礎(chǔ)教育以高考作為終極目標(biāo)。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,是實(shí)現(xiàn)階層向上流動(dòng)相對(duì)比較可靠的手段——既然這是明擺著的規(guī)律,用扎實(shí)的基礎(chǔ)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敲門磚,乃是必然。在穩(wěn)定的社會(huì)建設(shè)時(shí)期,普通家庭主要寄希望于通過(guò)高考改變孩子的命運(yùn)。即使考上個(gè)好大學(xué)不見得必然實(shí)現(xiàn)階層向上流動(dòng),至少還能維持在現(xiàn)有的階層,不致出現(xiàn)階層的滑落。
基礎(chǔ)教育階段沉重課業(yè)負(fù)擔(dān),根源在于基數(shù)巨大的同齡人在高考中競(jìng)爭(zhēng)稀缺的機(jī)遇。“減負(fù)”不會(huì)改變受教育群體巨大基數(shù)與有限的機(jī)遇總量之間的矛盾。因此,“減負(fù)”必然淪為形式主義的一陣風(fēng),根本不能解決任何實(shí)際問題。歐美國(guó)家所謂的“素質(zhì)教育”、“快樂教育”,說(shuō)穿了就是個(gè)荒誕不經(jīng)的神話:這些國(guó)家早在基礎(chǔ)教育階段就已經(jīng)實(shí)現(xiàn)了階級(jí)分化,普通人家的孩子讀教育水平一般的公立學(xué)校,用少年時(shí)沒心沒肺換來(lái)一生的卑微;有錢人家的孩子早早進(jìn)入精英學(xué)校讀書,課業(yè)負(fù)擔(dān)極中,何嘗不是咬著牙擠進(jìn)一流高校?
假如“減負(fù)”在中國(guó)真正得以實(shí)踐,對(duì)于沒后臺(tái)、沒背景的普通人家孩子必定是災(zāi)難——學(xué)校講授的知識(shí)越來(lái)越少,放學(xué)越來(lái)越早;普通人家的孩子在家玩手機(jī)打游戲,有錢人家的孩子參加價(jià)格不菲的私人培訓(xùn)班;最后誰(shuí)更有機(jī)會(huì)獲得優(yōu)質(zhì)高等教育的入場(chǎng)券,還用說(shuō)嗎?倘若不從根本上改變教育制度,只是片面地強(qiáng)調(diào)“減負(fù)”,最后的結(jié)果必然是學(xué)到歐美國(guó)家的糟粕,早早地在基礎(chǔ)教育階段就實(shí)現(xiàn)階級(jí)分化、為階層固化添磚加瓦。

中國(guó)教育陷入了“減負(fù)”—>無(wú)效—>再“減負(fù)”的循環(huán),圖片來(lái)源@視覺中國(guó)
教育系統(tǒng)內(nèi)充斥著思維僵化、因循守舊的官僚。他們沒有能力從國(guó)家戰(zhàn)略的層面來(lái)思考教育的意義,更缺乏制定科學(xué)合理頂層規(guī)劃的能力。說(shuō)句實(shí)在話,國(guó)家國(guó)防科技工業(yè)局遠(yuǎn)比教育官僚更清楚國(guó)家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。教育改革必須跳出反復(fù)“減負(fù)”的思維怪圈,直面教育領(lǐng)域的主要矛盾,即受教育群體巨大基數(shù)與有限的機(jī)遇總量之間的矛盾。
應(yīng)該厘清一個(gè)基本的邏輯:基礎(chǔ)教育階段的課業(yè)負(fù)擔(dān)取決于同齡人之間的競(jìng)爭(zhēng)烈度,競(jìng)爭(zhēng)烈度取決于社會(huì)提供的機(jī)遇總量。只有提高機(jī)遇總量,才能降低競(jìng)爭(zhēng)烈度,同齡人才不必在每個(gè)細(xì)節(jié)上一分高下。反之,如果不增加機(jī)遇總量,競(jìng)爭(zhēng)烈度就不可能降低。就算學(xué)校教得少管得少,同齡人之間還是會(huì)私下較量、以便一分高下。
因此,必須增加社會(huì)范圍內(nèi)的機(jī)遇總量,才能從源頭上改善基礎(chǔ)教育的生態(tài)。唯有如此,才能跳出“減負(fù)”這種“頭痛醫(yī)頭,腳痛醫(yī)腳”的思維怪圈。基礎(chǔ)教育的生態(tài)也確實(shí)需要改善,因?yàn)橹行W(xué)生課業(yè)負(fù)擔(dān)沉重,說(shuō)穿了還是過(guò)度競(jìng)爭(zhēng)、惡性競(jìng)爭(zhēng);基礎(chǔ)教育階段沉重的課業(yè)負(fù)擔(dān),本質(zhì)上是低水平的重復(fù)建設(shè),目的僅在于提高對(duì)有限知識(shí)集的熟練程度、用于應(yīng)付高考,而并不能夠很好地銜接高等教育。
如何增加機(jī)遇總量?出路在于高等教育的規(guī)范化建設(shè)。換個(gè)角度來(lái)說(shuō),基礎(chǔ)教育階段的過(guò)度競(jìng)爭(zhēng)、惡性競(jìng)爭(zhēng),源于高等教育創(chuàng)造的機(jī)遇總量不足,需要從改革高等教育入手來(lái)解決源頭性的問題。
理想狀態(tài)下,就讀“雙一流”大學(xué)的學(xué)生,作為國(guó)家棟梁會(huì)擁有較多的發(fā)展機(jī)遇;而就讀其他高校的學(xué)生,也應(yīng)該過(guò)上大致體面的生活。但實(shí)際狀況與理想狀態(tài)相去甚遠(yuǎn)——許多高校的畢業(yè)生在就業(yè)時(shí)遇到巨大的困難。畢業(yè)生當(dāng)然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,在自己喜歡的城市順利成家立業(yè)。但是站在用人單位的立場(chǎng)上看,這些畢業(yè)生的勞動(dòng)能力真的很成問題。用人單位要么不愿意聘用,要么只愿意以較低的待遇聘用、遠(yuǎn)低于畢業(yè)生本人的期待。
筆者就此深有感觸:朋友的生物科技公司招聘實(shí)驗(yàn)師,應(yīng)聘者中90%以上都是“菜鳥”級(jí)別的;中山大學(xué)的碩士,閱讀科學(xué)文獻(xiàn)的能力極差,用一個(gè)星期時(shí)間還弄不清實(shí)驗(yàn)設(shè)計(jì)的原理;幾個(gè)二本院校的碩士,除了做論文期間搗鼓的幾個(gè)簡(jiǎn)單實(shí)驗(yàn)之外,對(duì)其他的生物醫(yī)學(xué)知識(shí)缺乏起碼的了解。這幾位的業(yè)務(wù)能力不忍直視,薪酬期待卻是年薪20萬(wàn)外加住房公積金。說(shuō)實(shí)話,用人單位真沒有興趣請(qǐng)這幾位當(dāng)祖宗供著。
站在用人單位的立場(chǎng)上看,能夠培養(yǎng)“招之即來(lái),來(lái)之能戰(zhàn)”的高質(zhì)量畢業(yè)生的高校,其實(shí)為數(shù)不多。但是也只有這為數(shù)不多的高校,才能夠?yàn)楫厴I(yè)生提供真正意義上的發(fā)展空間和上升通道。在“千軍萬(wàn)馬過(guò)獨(dú)木橋”的格局下,過(guò)橋的和沒過(guò)橋的,能夠獲得的機(jī)遇有天壤之別——基礎(chǔ)教育階段的競(jìng)爭(zhēng)烈度能不高嗎?
畢業(yè)生期待與用人單位需求之間的突出矛盾,源頭在于我國(guó)許多高校的培養(yǎng)方式出現(xiàn)了嚴(yán)重偏差。教育理應(yīng)為社會(huì)化大生產(chǎn)服務(wù),以培養(yǎng)人的勞動(dòng)能力作為首要職責(zé)。而許多高校的教育導(dǎo)向,背離了培養(yǎng)人的勞動(dòng)能力這一根本性的方向,無(wú)法培養(yǎng)出合格的勞動(dòng)者。不合格的勞動(dòng)者,在社會(huì)上怎么可能獲得發(fā)展機(jī)遇和上升通道?
我國(guó)許多高校存在極為嚴(yán)重的教學(xué)資源浪費(fèi),因?yàn)闊o(wú)法培養(yǎng)合格的勞動(dòng)者,所以事實(shí)上并沒有增加社會(huì)范圍內(nèi)的機(jī)遇總量。就整體而言,許多高校對(duì)學(xué)生的學(xué)業(yè)要求流于自由散漫,造成了事實(shí)上的“嚴(yán)進(jìn)松出”——只要邁進(jìn)了高校的門檻,稀里糊涂混幾年,也能順利畢業(yè)。某些高校的部分專業(yè)和課程設(shè)置,其根本目的恐怕就是從教育部套經(jīng)費(fèi)圈錢——三流高校開設(shè)什么哲學(xué)、表演、藝術(shù)史之類的“務(wù)虛”專業(yè),這不是批量培養(yǎng)失業(yè)人口嗎?坦率地說(shuō),三流高校巧立名目開設(shè)的專業(yè),連起碼的師資力量都不具備,培養(yǎng)出來(lái)的畢業(yè)生不具備任何過(guò)硬的勞動(dòng)能力,能去私企做前臺(tái)都算燒高香了。
由此可見,改變現(xiàn)狀的根本途徑在于大力加強(qiáng)高校的規(guī)范化建設(shè),切實(shí)保證高校的教學(xué)資源有效轉(zhuǎn)化為社會(huì)范圍內(nèi)的機(jī)遇總量。說(shuō)得更直白一些,許多高校必須大力提高教學(xué)水平、增強(qiáng)對(duì)學(xué)生的學(xué)業(yè)要求,保證畢業(yè)生具備符合社會(huì)需求的、過(guò)硬的勞動(dòng)能力。欲達(dá)此目的,對(duì)我國(guó)許多高校進(jìn)行大刀闊斧的改革。
新一輪高校改革,應(yīng)當(dāng)以培養(yǎng)人的勞動(dòng)能力作為根本出發(fā)點(diǎn),樹立“教育為社會(huì)化大生產(chǎn)服務(wù),為社會(huì)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(shè)服務(wù)”的明確理念。將高校明確劃分為研究型高校和非研究型高校,研究型高校可以在基礎(chǔ)研究方面有較大的自由度,而非研究型高校的考核重點(diǎn)必須是畢業(yè)生的勞動(dòng)能力。進(jìn)入21世紀(jì)以來(lái),國(guó)內(nèi)某些高校喜歡打腫臉充胖子,胡亂開設(shè)一堆爛專業(yè),自詡“綜合性大學(xué)”。然而,不具備勞動(dòng)能力的畢業(yè)生等于廢品,這些高校顯然是有責(zé)任的。因此,非研究型高校應(yīng)該是未來(lái)高校改革的重點(diǎn)整治對(duì)象。具體的整治手段應(yīng)該包括:
1. 構(gòu)建高校之間的動(dòng)態(tài)競(jìng)爭(zhēng)和獎(jiǎng)懲機(jī)制。
非研究型大學(xué)教學(xué)水平的直觀反映,其實(shí)是畢業(yè)生的就業(yè)率和平均薪酬。就業(yè)市場(chǎng)其實(shí)是高度理性的。國(guó)家應(yīng)通過(guò)主流求職網(wǎng)站等大數(shù)據(jù)來(lái)源獲取這方面的客觀信息,作為考核評(píng)估非研究型大學(xué)的重要標(biāo)準(zhǔn)——你說(shuō)你們學(xué)校辦得好,可是畢業(yè)生連個(gè)像樣的飯碗都沒有,這可信嗎?如果高校畢業(yè)生的就業(yè)率和平均收入逐步攀升,說(shuō)明高校的培養(yǎng)水平被就業(yè)市場(chǎng)普遍認(rèn)可,這樣的非研究型高校就應(yīng)該獲得經(jīng)費(fèi)傾斜;反之,如果高校畢業(yè)生越混越慘,說(shuō)明高校主要領(lǐng)導(dǎo)無(wú)所作為,這就需要點(diǎn)懲罰手段以正綱紀(jì)。
2. 堅(jiān)決開展院系調(diào)整,裁汰不能培養(yǎng)勞動(dòng)能力的弱勢(shì)專業(yè)。
不鼓勵(lì)非研究型高校開設(shè)哲學(xué)、藝術(shù)史、社會(huì)學(xué)、國(guó)際關(guān)系等純文科專業(yè);某些專業(yè)的就業(yè)率如果連續(xù)幾年低迷,則必須停辦,促使非研究型高校將資源集中建設(shè)優(yōu)勢(shì)學(xué)科。
3. 加強(qiáng)勞動(dòng)能力的系統(tǒng)培養(yǎng)。
應(yīng)當(dāng)鼓勵(lì)高校從企業(yè)批量引進(jìn)客座講師、客座導(dǎo)師,在專業(yè)課上系統(tǒng)傳授社會(huì)和企業(yè)所需的勞動(dòng)能力;這既解決了課堂知識(shí)與實(shí)踐對(duì)接的問題,也有利于在校師生培養(yǎng)廣泛的社會(huì)關(guān)系。工科專業(yè)必須安排至少一學(xué)期的實(shí)習(xí)(校內(nèi)或校外皆可),杜絕紙上談兵。通過(guò)政策鼓勵(lì)校企結(jié)合,定向輸送專業(yè)人才。
4. 加強(qiáng)學(xué)生在校期間的學(xué)業(yè)要求。
教育主管部門應(yīng)當(dāng)積極鼓勵(lì)高校開除學(xué)業(yè)水平不符合要求的學(xué)生。許多高校學(xué)風(fēng)一塌糊涂,學(xué)生自由散漫,皆是因?yàn)楣芾硎е趯挕D呐率侨鞲咝#灰杏職忾_除5%的墊底學(xué)生,全校學(xué)風(fēng)立刻會(huì)提升一個(gè)檔次。
重點(diǎn)整治非研究型高校,切實(shí)保障高校能夠輸出具備過(guò)硬勞動(dòng)能力的人才,這就能夠解決畢業(yè)生期待與用人單位需求之間的突出矛盾。如果非研究型高校也能提供發(fā)展機(jī)遇和上升通道,全社會(huì)范圍內(nèi)機(jī)遇總量就會(huì)大大增加,基礎(chǔ)教育階段同齡人之間的競(jìng)爭(zhēng)烈度自然會(huì)隨之下降,也就沒有必要糾結(jié)于“減負(fù)”這個(gè)偽命題了。